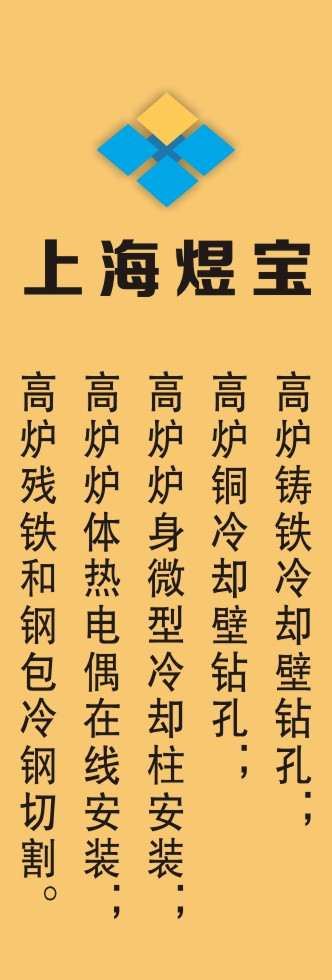-
最近又在翻看汪曾祺的《食事》。如果把文史哲之类严肃的书比作正餐的话,这本书就像是诸如拍黄瓜、海带丝之类的开胃小菜。
感觉汪曾祺的文字除了受其师沈从文的影响外,似乎还有些周作人的影子。虽然“净”不如沈从文,“淡”难比周作人,但揉和一下,自有平实淡爽的韵味,不媚不俗,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娓娓道来,文亦可亲。
端午要吃咸鸭蛋,而咸鸭蛋自然是高邮的最好。汪曾祺说在高邮,“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罗。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地亮,好看极了!”
在故乡淮北似乎没这个习俗,小时候也没看过这篇文章,所以没玩过这样的游戏,但萤火虫在夏夜里经常看到。那时已经有了电灯,不再需要囊萤夜读。室外乘凉的人不少,可大多摇着蒲扇拉着家常,没人手执青罗小扇扑流萤。于是,在我的记忆中,故乡的夏夜,经常是天上星光闪闪,身边萤火点点。
学过冰心的文章后,小桔灯倒是常做。不过,我做的桔灯大多如歪瓜裂枣,总是被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笑话,我因此还埋怨过母亲买的桔子有问题。
在故乡,端午的时候孩子们要撞鸡蛋。煮熟的鸡蛋装在小网兜里挂在脖子上,有得还用墨水涂成红或蓝色。到了学校里互相挑战,看谁的鸡蛋硬,撞破了别人的固然欢欣鼓舞,自己的鸡蛋被撞破了难免有点戚戚。
据说,有人做了个惟妙惟肖的木头鸡蛋涂上蓝墨水,由于百战百胜,最终引起怀疑被大家按倒在地验明真相。这件事我没有亲见,但我确实曾看过有同学鸡蛋被撞破后和泪吞蛋的场景,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被木蛋暗算的缘故。
二
汪曾祺有篇文章叫《切脍》。说来惭愧,一直把“脍”读成“hui”。后来一想,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不是有个成语叫“脍炙人口”么。
“脍”的意思是肉或鱼切成细丝或薄片,大多是指鱼,因为“脍”又写作“鲙”。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古人大概是切了沾点佐料生吃,似乎和吃刺身有点像。脍鱼不能用水洗,要用灰隔着一层纸去清理血水,这与日本的吃法肯定就不同了,而且“脍”的大多是内陆的鱼肉。以现代人的观念,能生吃的东西必然相当细嫩新鲜,比如深海鱼类和澳洲牛肉的某一极品部位。古今认知不同,那是因为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
汪曾祺的这篇文章引起我的兴趣,因为“脍”让我立刻想起了辛弃疾。他的一首我个人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里有这样的名句:“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很奇怪,鲈鱼现在寻常见,经常吃,没觉得有多好吃。
不过,我最喜欢词里的这两句:“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三
汪曾祺《寻常茶话》中谈到滇红,认为比祁红、英(英德)红都要好。
口味各不相同。英红我没喝过,现在刚出的信(信阳)红也没有喝过。就滇红和祁红而言,我比较喜欢滇红。它有一种特殊的果香,而且比较耐泡,价格也亲民。二三百元一斤的滇红味道已经非常不错,买上一斤,可以喝上大半个冬天。
有时候,喝茶喝的是心境。前不久回老家,同学请我到古镇临涣的茶馆里去喝棒棒茶。所谓的棒棒茶其实就是红茶的茶叶梗,茶壶和茶碗也只是土陶所制。几个老同学坐在一起喝着茶聊着天,气氛很融洽。端起茶碗喝上两口,嗯,茶很甘甜。同学说,临涣的水好,只有配上这里的水,棒棒茶才有这样的味道。
(责任编辑:zgl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