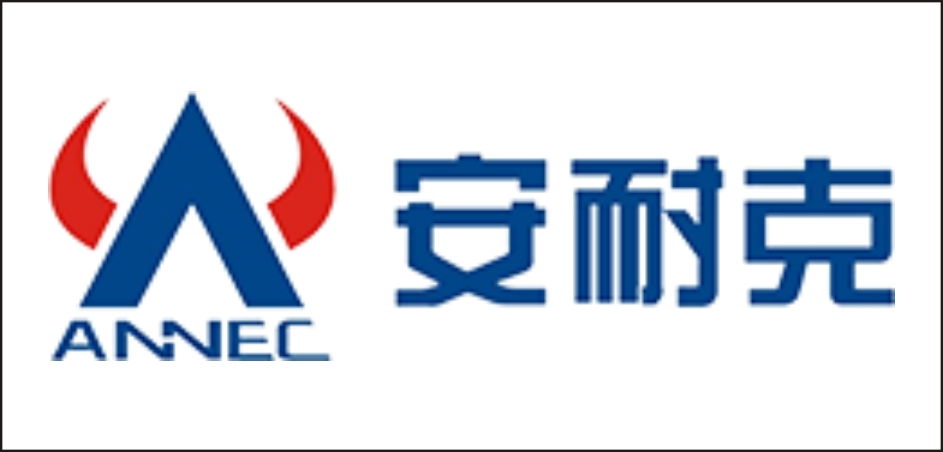-
我的记忆里,爷爷一生都在耕地,别人回家时,肩上扛着铁锨、锄头,爷爷却扛着一副大铁犁;回到家,他把犁挂在墙上,休息时两眼跟着犁的框架画那粗粗的撇捺。想到怎样改造铧的角度、犁的盘架,能使犁沟深一点,爷爷魔怔一般,突然坐起,不是斧刃削削木犁,就是磨石磨铧。
营务庄稼,得分种、浇、肥、锄、收,可从没见过爷爷坐在车辕上,插起鞭杆,任马识途慢慢走;每天天不亮,爷爷就扛着犁,拿着牛跟头(也叫牛梭头或牛轭,耕地时套在牛颈上的曲木,是牛犁地时的重要农具,与犁铧配套使用),挑一个最强健的牛,村东村西、庄南庄北去犁地。 只要我起床看不见家里人,就去庄南找爷爷。千亩良田里回荡着牛犁地的喔喔声,看着远远的黑点移动,我知道陪伴我的,只有这些背景和电线上两串串的燕子。
爷爷是有原则的人,犁地时犁不出亩数来,他不会停歇,有时看着他陷在深深的犁沟里,一寸不掉地跟在牛的后边,十分劳累,大家就劝爷爷犁浅点,人好走。可爷爷说,犁、耧、耙、磨都是良心活,可以肤浅地应付,但种出的庄稼收成差,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获,所以糊弄不得。犁过8分地后,爷爷才停下犁,让牛休息,这时我就想替爷爷在那千亩的良田里耕个来回,但犁重的扶不住,不听话的牛打不走,它还回头、恨眼、撂尾巴,把我一次次扶起的犁弄倒下。
爷爷怕我无趣,就带着我在犁过的土地里刨东西,渭北有套种庄稼的习惯,收挖时有遗漏,犁地仿佛篦梳式翻地,所有遗落,在一铧一铧中翻出。因而有些地方可以刨出红苕,有些地方可以刨出花生,还有些地方可以刨出玉米棒子等,这些意外和惊喜让我兴奋不已。
爷爷深犁翻过的土地,光脚踏在松软的土里,随意翻着跟头,四肢肆意舒展,身体任一处触碰着土,犹如跌落在奶奶的怀抱,那种宽宥呵护的感觉,自由自在的任性、随性洒脱的心灵,在这一刻不为天地约束,不为别人言行牵绊,畅快如风,惬意至极;加之,蠕虫翻出,百鸟随犁,又大又红的太阳悬在村与土地之间,一幅幅百鸟散还合,万里晨曦一片红的画面展现在眼前,格外的美丽。
休息的时候,爷爷从牛身上解下犁,一手牵牛,一手牵我,让沉重的犁铧趴在背上,我就问爷爷:“背着大铁犁不重吗?”爷爷说,不重!犁是种收的头绪,不耕哪来的种收?种下希望,收获和期待是最大的幸福。
我也曾经幻想给犁按上轮子,可看到沟渠梁坡、田深畔高,想哪犁装了轮子,也未必在坎坎坷坷的土地里行走超乎爷爷轻快。故而,爷爷再犁地时,我就安定地坐在土地上,看那燕子向我飞来又飞走,看那蚂蚱被被土压着弹不起身,看爷爷扬鞭斥牛扬起的尘土,看那一铧一铧翻出清新的沟壑,嗅着深层里散发的庄稼味道,想象着爷爷为大地要丰收的倔犟和不懈奋斗的神情。
(责任编辑:chen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