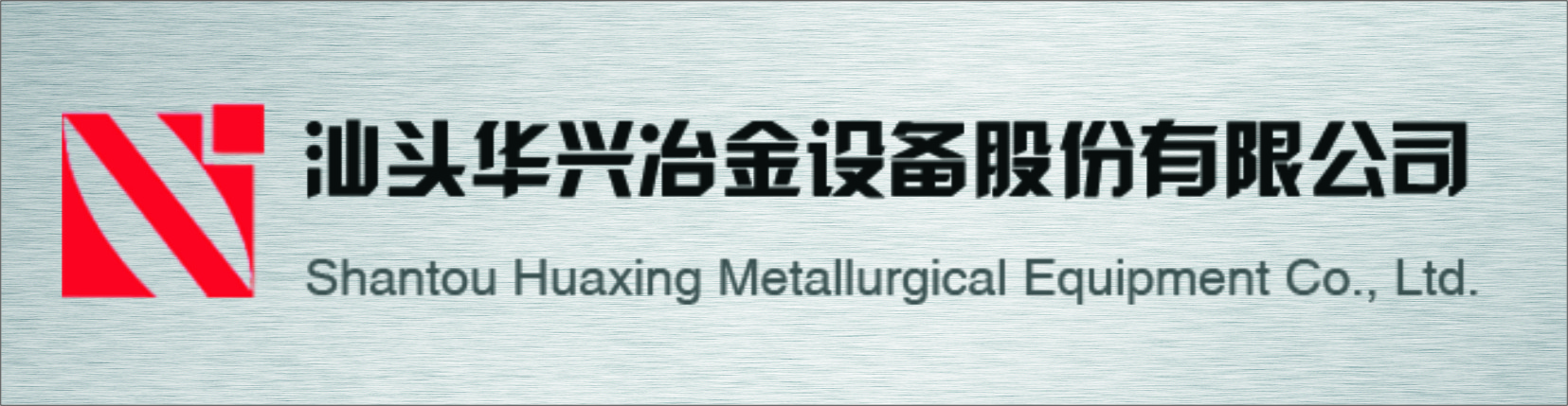-
故乡,是我们出生的地方;
故乡,是我们心心念念的地方;
故乡,是我们为之倾注了最好时光的地方...
离开高炉好些年了,有些记忆被经年的风吹雨打褪却了颜色,就像儿时大门上贴的对联,经历过初夏秋冬四季的侵蚀后,留下的只有淡淡的痕迹,有时连那些痕迹也荡然无存了。可有些记忆却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也许只是不经意的一个旧人,或许是一首曾经的老歌,瞬间便把你拽了进去,久久不能自拔。
去年夏天一个湿塌塌的下午,忽然听到了二号高炉要拆除的消息,诧异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怔怔地瞟向窗外,细雨如丝,天空灰暗。踱到窗前,目光穿过雨幕,掠过树梢一片亮晶晶的叶子,越过一个高高的烟筒,汇入到灰蒙蒙的天空中。
天空混沌一片,思绪杂沓纷至,二高炉的往事犹如一个碎成一片一片的盘子,散落在荒野中。对于我们包钢来说,这座1960年建成,2004年大修的高炉可谓战功累累;对于我个人来说,它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就是在这座当年被称为全国“三大危炉”之一的炉子上,我跌打滚爬了整整五年。
二十多年的那个腊月,一号高炉炉缸冻结,如同一个重病患者,正在一点点调养回复。沉重的担子落在了已经是风烛残年的二号高炉身上。作为一个车间主任到公司开会是很少见的。那一年,我去了。领导问题很简单,二号高炉能不能挺到年后停炉?若是在年前停下来,高炉煤气不够,焦炉的生产势必受到影响,职工们家中使用的煤气就要断了,年过不好。如今回想,似乎很好笑也很荒唐,细细品味,却是另外的一种滋味。
那一年的年夜很冷,留在我记忆中的是一盆又一盆热气腾腾的饺子上了炉子。印象最深的是几个炉前兄弟抓起几个饺子塞到嘴里,鼓着腮帮子向外跑。饺子里的油顺着嘴角溢出来,他们随手抹了一把,嘴便黑了。临出门,他们还瞟着盆说:“给我留点!我忙完就回来吃。”
苦、累、险,真不觉得,高炉上那些弟兄们也不觉得。炉子虽然残破不堪,但那种劲头和火热的氛围过去这么多年了,依然历历在目。
心里忽然萌生出一个念头,去看看它,就是现在!老天仿佛跟我过不去,细细的雨丝密了也粗了,刚刚还润物无声,转瞬间便沙沙沙地响了起来。风骤起,卷着细碎的水珠扑面而来,一个穿着老式帆布雨衣的男人出现在视野。雨虽然很大,他走的却不紧不慢。
我定定地瞧着他,脑海中浮现出了当年的配管大班长老郭。高炉后期,配管既危险又辛苦,整个炉子由于冷却壁的破损,炉皮变形,到处支着水管打水,犹如水帘洞。配管工每天穿着雨衣在工作,但那一层薄薄的塑料布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遇到哪里的炉皮红了,他们都是没命地跑着过去,拽起嗤向别处的水管对准发红部位一阵猛嗤。一股股浓浓的白气顿时腾起,炉皮遮挡回来带着温度的水劈头盖脸地浇在身上。水从领口、袖口灌了进来,又顺着裤脚滴答嘀嗒地滴落在风口平台的的砖上。
很多人见过高炉出铁,但你见过在铁沟上搭着临时棚子出铁的吗?那年的二高炉就是这样,由于从炉顶到风口到处都是水,出铁时,怕水进到铁沟里放炮,配管和炉前的弟兄们每次出铁前先要在铁沟上方用铁管和瓦楞板支起一个长长的棚子。出完铁后,那棚子被炙热的铁水烤塌了,下次出铁前又重新搭,周而复始。
那年从年三十到初五几乎都是在炉子上度过,累算不得什么,关键是睏。高炉工长室紧挨着放风阀,好多次都是在那里杵着锹把子就睡着了。也不一定是什么声音会让我霍然惊醒,睡意顿消,瞬间又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了。
如今回顾,自己都不明白当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窗外的雨根本就没有停歇下来的意思,心却急不可待,拎起桌角的伞毅然钻入雨幕。雨水冰凉,心里火热,趟着马路边的积水到了二号高炉,忽然感觉它离自己如此得近。就是这么短短的一段路,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想着过来看看。
鞋里灌满了雨水,身上湿了大半。说也奇怪,雨却如同踩了急刹车,说停便停了,停的干净利索,丝毫不拖泥带水。因为雨水冲刷的缘故,挤在一三高炉中间的二高炉看着湿淋淋的新鲜。脚步滞重,脸向上仰,轻柔的目光久久地抚摸着高炉粗糙的肌肤。无由来,眼睛微微发酸,伤感瞬间从每一个神经末梢弥漫开来。踱到高炉的楼梯口,却停下来脚步,不想上去了,真的不想上去了。
心里默默地念着:别了,我的老哥,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我那年初六离开你后,去了四号高炉。四号高炉其实就是你的延续,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的四号高炉是用你易地大修的名义建起来的。你知道吗?好多当年的弟兄说,四号高炉的开炉你是怎么顶下来的?说句实在话,都说四高炉开炉艰苦,我真的没觉得什么。如今回想,我的人生因为经历过你,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我的事了。
别了,我的老哥。
(责任编辑:zgltw)